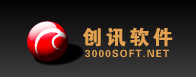“大珠”要成為世界印刷中心,不是要拼規模,拼產值,而要拼特色、拼技術、拼服務。
“大珠”包括珠三角和港澳,人們很容易認為,既然香港已被公認為世界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大珠”可以說是香港的延伸,“大珠”應該自然會成為世界印刷中心。我覺得這個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關于世界印刷中心的稱呼,我認為一不是自封的,二不是哪個組織命名的,三是動態的,不會是永久不變的。
當然能稱之為世界印刷中心,在大家的心目中是有一定標準的。現在大家公認的世界四在印刷中心:美國、法、日本和中國香港,前三位是以綜合實力、生產規模、技術水平、經營管理、市場服務等等雄居世界前列,而成為世界印刷中心的,而香港則是以其技術精湛、管理嚴格、市場開放程度高、外向型經營、服務周到等這些鮮明特色而吸引世界。
上個世紀80年代,我曾兩到香港考察,那時香港印刷來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期。香港作為世界貿易自由港,吸引了世界許多廠商到香港投資,但香港又彈丸之地,狹小地區不可能接納大型機械制造等工業,因此電子、服裝以及印刷這些技術要求高而占地相對小的產業很快發展起來。日本最大的兩個印刷企業:大日本和凸版印刷公司先后在香港建廠,這兩個印刷公司采用世界先進印刷技術,加速了香港印刷業的競爭。當時香港的中華和商務兩印刷廠曾在香港印刷業首屈一指,但由于受文革的影響,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落后,幸虧他們及時采取對策,從1980年開始,將中華和商務合并重組,成立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公司,加快技術改造,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裝備,同時面向世界,為了吸引海外客戶,他們不斷在印品質量、服務上下功夫。1988年“中商”的營業額比1980年增長了8倍,利潤增長了5倍,其中彩印的海外營業占到70%。
香港中華商務走過的道路是香港印刷業的一個縮影。據統計,從1982年到1997年,香港印刷年產值增長7倍,年產值達到300多億港元,成為香港第三大支柱產業,其中100億是承接海外的營業額,占總產值的1/3,而其中50億出口到美國,占美國進口170億元的30%左右,香港成為美國最大的印刷品進口商(以上數據引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曾昭學主任發言),香港因此被公認為世界印刷中心之一。
從香港走過的道路,我認為“大珠”要成為世界印刷中心,不是要拼規模、拼產值,而是要拼特色、拼技術、拼服務,要放寬政策、堅持特色、發揮優勢、繼續走外向型發展的道路。
從這一點出發,必須從各個方面研究制訂為使“大珠”成為世界印刷中心相應的政策措施,改革一切不相適應的政策法規,創造相應的政策環境,包括投資、增資、地區性保護、出版物印刷審批、外資企業設置分支機構、外商投資印刷企業條件、關稅等等方面。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仔細研究逐項落實。我們很多情況是,由于一個環節脫節,常常影響全局,而功虧一簣。CEPA的簽訂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但是落實這些政策措施需要作更大努力。
如果“大珠”既具有先進技術和外向型經營的“硬”環境,又有保障正常運營的相應政策的“軟”環境,那么成為世界印刷中心應該是完全可能的,也會對我國其他地區印刷業的發展起到示范、借鑒推動作用。當然,這不是“國”字號而“特”字號意義的世界印刷中心。
我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市場需求量非常大。我們現在2000多億元的印刷產值,在13億人口里面,只及發達國家人均1/10。所以當“大珠”成為外向型的世界印刷中心的進修,不僅不會影響其他區域和其他地區印刷業的發展,相反而是會更加促進它們的發展。在這方面,我國經濟界有一個發揮比較優勢的理論,很值得我們研究。現在我們與發達國家在綜合實力上有較大差距,如果我們全面趕超則可能欲速不達,而如果我們發揮自己的特長,在自己的優勢方面加大努力,有可能出奇制勝,突破一點,帶動全局。
因此我們在研究區域印刷產業發展戰略的時候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發揮比較優勢,研究規劃時不一定要像美國、德國、日本那樣整個國家成為世界印刷中心,可以在一個區域率先突破建世界級的但有鮮明特色的印刷中心,其他區域可以成為地區級、國家級的印刷基地,這樣我國區域印刷產業有世界級的、地區級的、國家級等各個層次。到那個時候,我國可能在綜合實力上能夠成為世界印刷中心,我想這個目標在本世紀能夠實現。(作者:沈忠康)
|